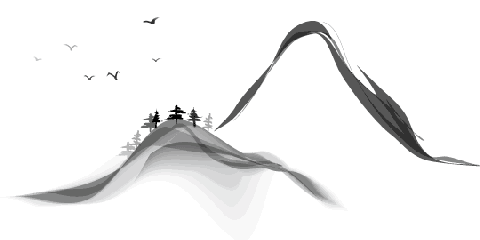当大娄山沿着云贵高原一路潇洒地走来,低下高昂的头颅,放下挺拔的身段,伸进千里乌江,将骨肉与血脉揉进涛涛乌江水,完美地画上句号,化为浩瀚大海的一个惊叹号后,却在逶迤的金子岩留下许多抹不去删不掉的记忆和故事。龙口垭祈雨
那天,是雨后天晴,和友人驱车前往龙口垭,沿途鸟鸣犬吠,扎眼的新式楼房鳞次栉比,白墙灰瓦,红墙翘檐,满庭芳菲,被午阳照耀得光彩夺目,山的气息和泥土的芳香带着花的玩味如丝如雾从车窗缝隙里涌入,音箱里缓缓流动的《仙女山的月亮》也被淹没。满山碧翠刺眼,徐徐山风醉心。
我们第一个目标直奔龙口垭。龙口垭是位于金子岩中的一个山垭,远远望去,一遍葱茏,看不到一丁点裸露的岩石和泥土。当我们穿行在刚开挖的林间道路上,习习山风,丝丝凉意,把心扉陶醉,把尘世幻化。一颗颗高挺的松树挤挤挨挨,相互拥着,不离不弃,密匝匝的针叶只许阳光微投。人在其中,没有红尘的骚扰,更没有喧嚣的烦躁,只有松涛的旋律似归途的《回家》。
龙口垭是在两个山头之间的一个缺口,站在那,便可见扬鞭奋蹄的骏马驰骋马鞍山,传说中的吴刚在月亮山下饮水芙蓉江。早年从垭口悬挂在崖壁的羊肠小道,就是谭家村和史家村(现合并谭家村)村民通往江口古镇的必经之路,也是大家赶场去来歇息吹牛摆龙门阵的幺店子。如今小路荒芜无人眷顾,只有一串记忆留在百姓心中。
我们攀上左边的小山头,一方呈长方体的石碑矗立山巅,碑高约一米许,宽两巴掌有余。这块立于民国十六年春月的石碑虽小,但承载着近百年的风雨历程。正面上方“顶敬”二字从右到左分开,“祈雨坛师披发授旨三界显灵法兴仙·香位”主旨碑文居中;右刻“敢则有应”,左刻“叩之必灵”,罗姓、舒姓、代姓、汪姓、郑姓等八位信善弟子分刻主旨碑文两边;六十名信众分别刻于碑的左右两侧,杨邦道、向国辉、李象之、肖世昌、刘世福、杨白云等江口的有名乡绅、社会贤达也列其中。碑小乾坤大,寄予了百姓渴望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美好希冀。
垭口右侧被林木掩映中,一个山洞正对祈雨碑,洞内钟乳林立,形状奇特,有的大可擎天,有的小似牙签,晶莹透亮的岩滴水在倒挂的石幔上悠闲自得。洞口若张开的鲢鱼口,上唇布满肉齿,牙龈上一圈锋利的虎齿让人寒栗。当地百姓称其为“龙口”,形象逼真,大娄山、金子岩就是升腾起的龙身,于是“龙口垭”就应运而生。
早年,山民百姓靠山吃山,没有科学的种植方法,也没增产的良种,传统农业,沿袭刀耕火种,开山扩地,无论是包谷、洋芋,还是红苕杂粮,种广大坡,生怕遗漏那块土地,山秃了,水断流了,人一辈辈地弯下了挺直的腰,还是吃不饱穿不暖。遇上久旱不雨,庄家面临颗粒无收,他们想起了龙口垭的祈雨碑,便成群前往拜谒,祈求老天开恩。我不知道老天真下雨没有,但我知道是他们的虔诚和渴望。
这,算是我知晓的龙口垭吧!
野猪凼观景
顺龙口垭的步道向右登上另一个山头,就是当地百姓命名的“野猪凼”,也有墨客赋予美名“鹤鸣岩”。由于林深人迹罕至,四面环山,中间一凹陷的平地,是野猪聚集藏身的最佳场所,常有野猪栖息。如今却成为远近游人慕名的打卡地。
林中步道旁一颗神奇的松树令游人驻足观望,啧啧称奇。树干粗一人合围,高六丈有余,在距树巅略数尺处,四周突然生出许多松枝新芽,蓬松密集,风不透雨不湿,如冠如球,径不下一丈,周身泛着绿光,似生命在舞动。在游人私语和嘈杂的喧闹声中,一只猫头长尾的动物从中展翅飞走,大家惊奇地睁着一双双眼睛呆若木鸡。有人要鼓掌吆喝,看里面还有没有藏着的,我赶紧止住:“大家轻点,别扰它们的宁静,赶快走吧。”于是我掏出手机拨通了村里社里的干部电话:“野猪凼这住着猫似的松鼠,告诉村民们,要好好的保护,没事别到树下吵闹惊扰,更不能砍伐周围的各种林木……”我不敢瞎猜,也不敢意会,上网查阅资料,据说科学家在澳洲发现过一个全新的物种,这种生物有着形似家猫的头部和鸮形目的身体,发现者将其命名为鹰身猫面兽。是否此物种,有待观察和论证。
仅隔几步之遥,便来到野猪凼观景台。茂密的松林里,荆棘杂物被清除,“好事者”在临崖的一堆高低错落的石林里,选择其中高凸傲然而平整的石面上篆刻“观景台”三个鎏金大字,大家看着闪着光芒的篆书字刻,举起手机拍个不停。信步登上观景台,仰望高天,苍穹蔚蓝,云丝悠悠,梦幻星辰,天河鹊桥,牛郎织女……在脑际闪烁;俯瞰峡江,乌江、芙蓉江不期而遇,想象中交织成河向长江、向大海而去,夏日里,浪花淘尽英雄,浊洗涤苍生。可初夏的今天例外,江水格外的蓝,蓝得刺眼,蓝得深邃,静若处子,平如镜面。从北岸伸进水面的偌大碛坝好似要截断乌江云雨,一块狭长的碛坝如弯月漂浮在蓝蓝的江面,一条长长的堤坝像一根导线链接着水中扇形碛坝,似飘落的树叶闪着金光,静静地躺在水面。芙蓉江汇入乌江口处的芙蓉江大桥,用半百的履历和上街下街对话,用默不作声的榜样为子民示范,畅了319,活了川湘道。岸边沉睡的古镇睁着惺忪的眼睛,用一栋栋崭新的楼房,一排排古韵犹存的街市伸展着腰姿,将两江交汇的陆岸妆点。中学和小学位于古镇东西两端,成持莘莘学蒙鼎新革故,传承历史文化开拓未来。全兴酒楼边,千年黄桷树下“李进士故里”巨幅摩崖石刻,静听江河潮起潮落,滋养两江学子润物无声。一代宰相魂附令旗山薄刀岭一千三百余载;干支木木牍、遣策、告地书在江边沉睡两千多年,大量的史实把江口推向远古的时空。两堤锁大江,高峡出平湖,昔日的蛮荒之地流放之所,如今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敞开心扉为西部大开发,为双城经济圈,印了“两江福地,千年江口”的美称。
站在野猪凼观景台,何止观景?相信眼皮底下的古镇还有难以数尽的故事!
金子岩叙旧
我老家门前五百米之处就是金子岩黄金段,悬崖绝壁,岩石明晃,望而生畏,一条通往古镇江口的手爬脚蹬的小路就从山崖像绳索一样被丢向山根,那是我们生产队里出行的必选路径。过去的千百年,乡民守着金子岩受穷,而今华丽转身,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乡村在小康路上快跑。岩边有座观音庙,庙虽小,但有故事。
传说,金子岩上有个肖二娃,家贫如洗,父亲早逝,母亲外嫁他乡,和残疾的哥哥相依为命。这天讨饭归来,饿晕在金子岩边的庙前。第二天早上从睡梦中醒来:一位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老人,慈祥和蔼,端给他一碗米饭,送给他一块金砖。想起梦中的米饭,更是饥肠辘辘,米饭随梦醒消失,随手一摸,但金砖还奇迹般在身边。他睁眼细瞧。砖块黢黑无比,可肖二娃想起白发老人的叮嘱:“我叫金砖把颜色变,拿着走路才安全;你进家门把它唤,自然就会成金。”肖二娃伸伸腰,倍感精神振奋,他如风一般走过山岩,跑进家中。手中的砖头变得金光耀眼,哥哥莫名其妙睁大双眼。肖二娃这才一五一十道出梦中奇缘。哥俩的生活很快得到了转机。“金砖保你一时,勤劳保你一世。度过难关之后,你一定要勤俭持家,切莫好吃懒做,荒废一生。”想起这些,肖二娃更加勤劳,还给残疾哥哥娶了媳妇,生了胖小子,过着富足美满的小日子。
后来,当肖二娃谈婚论嫁时,哥哥百般阻挠,原来是怕肖二娃的孩子分家产。哥哥的这些小九九,早被二娃的嫂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善良的她屈服了蛮横的丈夫,弟弟娶媳妇也就成了她的心病。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哥哥暴病而去。二娃哭得比嫂嫂和侄儿还伤心:“哥哥哟,哥哥,你这么早就走了,嫂嫂和侄儿他们母子俩,今后怎么办哟?阎王爷,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呢?把哥哥留下,跟嫂嫂和侄儿一起,好好过日子……”二娃哭得天昏地暗,邻里乡亲无不动容。后来,按乡里风俗,弟也可以填房娶嫂为妻,肖二娃一肩挑起了家庭重担,对嫂嫂和侄儿更加照顾,体贴入微。肖二娃发誓不再生孩子,要做到爸胜亲爸,子胜亲子。善良的肖二娃梦里得金砖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并流传开来,人们便把村子里的那面山岩奉为神山,叫做金子岩。
想起曾经的祖祖辈辈,在金子岩口,生产生活物资肩挑背扛进山,山货木材披星戴月出山,祖宗从没想到挂壁路变成如今的连接桂花、广杨、黄莺乃至贵州的水泥公路。望着南来北往穿梭的车辆,我又想起十多年前从村里修往我老家农业社的这条近5公里的支路。我老家农业社如今叫白杨坨农业社,是一个只有20户不足100人的袖珍小社,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规模的产业,没有可运往山外的资源,公路修进山就是尽头,没了去处,成为断头路,谁还愿投资几百万?
这年,我和在外打拼的兄弟几人,私下约定,你两千,他三千,我五千的自愿筹款,鼓励家乡父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主动改变落后交通。
这天,村里书记、村长在我家老屋主持召开的修路会议,远在北京门头沟矿井里的友国兄弟,生长在石桥乡八角村的兴明,临社的兴华等晚辈随我们杨氏、肖氏的兄弟们,抱着三万多元现款出现在会场。和大家一起定路线、分任务、明职责;遇到石山硬茬,打炮机、挖掘机来了;开挖路基要占地,杨家屋后、黄家门前的菜园地无偿用就是,不谈价钱;加宽改直宽度不够,退伍老军人杨武乾和弟弟杨武寿的猪圈、柴棚,自己拆除掀掉就是,不要赔偿;买雷管、炸药等爆炸物资钱不够,你三百他两百,人人都捐个个都投……一条5米宽的入社路成型了。
这时,白杨坨淳朴的民风,图强的精神让各级领导感动,镇政府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多渠道筹集资金,寻找施工队伍,监管工程质量,一条平整宽阔的“幸福路”伸进了古老而落后的白杨坨。
不等百年,这些都会变成故事!
梨子坪踏春
在金子岩对望蔡家村的梨子坪,山形、海拔、物产、民风民俗如此的相似,但我却熟悉而陌生,没有亲临现场,没有置身其中。山下319国道跨越九十个春秋,地下艺术宫殿芙蓉洞露了三十年的笑脸,一江芙蓉水作证,两个奶子山可鉴。那天,我和一群文友举着“文学在场”的旗帜走进了这个村庄的梨子坪茶山。
入山口的一段3公里崎岖道路颠簸得让一行人纳闷:“这个年头还有这么难走的公路?”周老板担心我们的轿车无法进山,早早地开着越野在路口等着。车到尽头,才知道,这是荒废了近五十年无人问津的茶场,党委政府和村支两委正引进企业老板,把资金在梨子坪扎根,让技术在梨子坪结果。一条5米5宽的产业路正从山顶往山下铸造。
刚入茶园,立体的山脊满目阶梯形的茶树,一台一台往上伸展,直至山顶。茶树修剪整齐划一,嫩绿叶片挂满树丫,夕阳下光点闪烁。刚硬化的水泥公路直插几百亩的茶园腹地,为山外开僻了来路,为茶叶找到了归途。八十岁的老支书面对欣喜的作家们,更是喜形于色:“我们这遍茶山呀,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那时的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因地制宜,山上发展经济作物,山下种植大宗粮食,形成‘山上有银行,山下有粮仓’的发展格局。乡党委、政府领导包片发展从云南普洱引进的茶业,下雨天不能生产劳动,就带领社员挖生土、开荒地、改茶山、修茶厂,派副业大队长任厂长,各生产队派青壮年劳力专门管理经营茶山。”说到这,老书记顿了顿:“我们这茶山啊,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由于粮食不够吃,每个人都想回家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茶厂就没人管理寿终正寝了。”望着几座修剪打理得生机盎然的茶山,老书记似又看到了希望:“这些年,镇上想方设法开僻挣钱路子,利用闲置资产,引进外地资金技术,鼓励回乡青年创业,营造良好经营环境。周老板来了,自古没有的公路有了,荒废的茶树复活了……”
夕阳西下,站在崖边,听着老书记激动的话语,遥望远山的金子岩在时空中漫漶,低头俯视月亮山被翡翠的芙蓉江环绕成规则的椎体,凝似万里沙早已遁迹的九曲黄河,也如草原荡气回肠的莫日格勒河,晚霞穿过朦胧的半空撒落在山尖,旋即在芙蓉洞前点亮了武隆高亢的旅游之歌:“幽远时空·化境武隆”,凝结成一部武隆旅游发展的真实史册,她的名字叫“天方夜谭”。
杨武均,男,汉族, 生于1963年10月。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学,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散文学会会员,武隆区作家协会秘书长。爱好文化散文,《家风祖训铸就的武隆文化地标》《梦幻情丝》《电视人生》《古镇记忆》《薅草歌》《哭嫁歌》《进士遗风》《大塘路上走“官桥”》《三十的火十五的灯》《青山处处埋忠骨》等多篇散文散见《今日头条》《搜狐网》《重庆日报网》《芙蓉江》《武隆日报》等报刊。